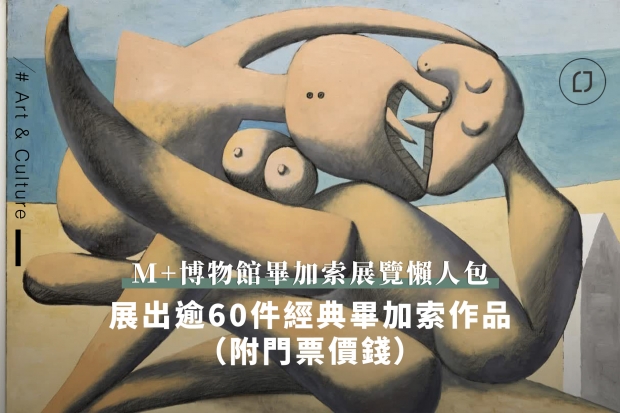林艷虹鑑賞天地: 字典藏家見證時代文化變遷
 Jonathan最有興趣研究不同英語學習詞典如何處理句型。
Jonathan最有興趣研究不同英語學習詞典如何處理句型。 初中時代第一本購買的《牛津高階》(英英)第三版,具有紀念價值。
初中時代第一本購買的《牛津高階》(英英)第三版,具有紀念價值。
隨着社會急速發展,新詞湧現,香港人常用的牛津辭典也與時並進,最新收錄近幾年網上流行的千多個潮語,包括山寨、惡搞、斷背、憤青、自由行等,連「囧樣」都有,趣味盎然。可是,在香港緊張忙碌的生活節奏當中,除了考試、做功課以外,有幾多人願意重拾字典學習英文?港人的英語水平下跌又是什麼因由?香港大學應用語言學博士生魏寶雲(Jonathan)喜愛收藏新舊字典,同時研究早期香港英語詞典的編纂背景和文本內容,見證着字典與英語學習的時代變遷。
九七後港人英語水平,一如傳出美國聯儲局部署退市消息後的股市,每況愈下。由國際教育機構EF (Education First)發表的「EF英語能力指標」顯示,去年全球五十四個非英語為母語的國家或地區中,香港排第二十五位,較2011年急跌十三位,被排第十二的新加坡遠遠拋離,更比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和韓國還要低,而且是唯一退步的亞洲地區。
也有網上英語學習機構公布的2013年度商業英語指數調查,發現非英語為母語的人士中,香港人的商業英語排名第二十一位,較去年大幅下跌九位,不禁令人憂慮香港在國際間的形象和競爭力。
本地教育向來側重應試技巧,早已為人詬病,小學生英語被評水平低,連在職人士與高官的英語水平同樣差強人意。Jonathan想起一個例子,有位本地高官在一次訪問中將「列出市民擔憂」,說成「list out people's concern」,他疑惑:「為什麼要用out?list是及物動詞(transitive verb),後面直接跟object,這裏不是point out something,而是list something,用out是受中文語言所誤導,所以學習一個生字,如果不肯定就要查字典,減低講寫英語出錯的機會。」
現時科學昌明,除了傳統的印刷字典,網上有許多學習英語的資源和渠道,連手機也可以當成電子辭典般「每天篤」,反而港人英語水平大倒退,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港人學不好英語?
「第一是缺乏興趣,第二是日常生活和工作較少機會接觸英文,第三是用錯方法。」Jonathan當過英語教師,常見學生學英語生字、查生字的時候,只會看中文意思,沒有深究其用法、句型、詞性、發音、同意詞、反義詞等等。「句型尤其重要,高中或以上學生,講寫英文時所犯的病句,不少是和句型有關。」
 第一位編著英語學習字典的中國人鄺其照。
第一位編著英語學習字典的中國人鄺其照。 Jonathan收藏的《華英字典集成》第三版內有鄺其照的題字及簽名。
Jonathan收藏的《華英字典集成》第三版內有鄺其照的題字及簽名。
最簡單但常犯的例子是「glad」,同義詞great、good、nice都可以放在同一句型「it's nice to see you」,但並沒有「it's glad to see you」。「正確是用人稱如I am glad to see you,不過這些錯誤,我也聽成年人犯過。」
英語詞典是自修英文的有效工具,他認為查字典時,要多留意常用字的意義、短語、搭配和句型。另一方面,要學好英語,最基本是從三千個英語常用字着手。「這是英文最重要的部分,每個常用字用法千變萬化,也是最難掌握。如能靈活善用,英語能力必然大增。」
可是,有些學校控制不好,任由學生揀剪報,結果學懂艱澀難明的字,但對日常生活未必有幫助,他舉例:「英語lazy大家都曉,indolent意思一樣,但至今只有一位英國劍橋大學的老師跟我說indolent,這個字文縐縐,實用性低。其他深字如uxorious(寵愛老婆)、henpecked(懼怕老婆)也很精警,但太formal,純為興趣不太實用,學生不會怕老婆、驕縱老婆,不過貪得意都會教學生。」
林語堂說過:「學英文時須學全句,勿專念單字。學時須把全句語法、語音及腔調整句學來。」Jonathan亦不主張背字典,認為背誦失去語境意義。「在十九世紀,有位法國語言學家往德國居住,出發前將整本德語字典背熟,但是去到當地卻完全溝通不到。這種純背單字,沒有例題和應用,根本不可行。等於在香港,除非身邊有許多外國朋友,或者喜歡聽西洋音樂、看西片,英語才會進步。」
看字典是學習英語的其中一個方法,不過大量閱讀才是最佳妙法。他建議無論是小說或中國歷史書,也可選擇閱讀西方學者或中國學者的英文版本,其中Jonathan D. Spence是他最欣賞的作家。「他的英文非常出色,尤其是寫中國歷史書方面,做了很多研究,考究充足,加上以文學筆調寫作,吸引很多美國人和英國人追看。」
Jonathan家中如一個迷你圖書館,書房、客廳書櫃放滿大小不同的書籍,而且還有一間字典房,收藏約三百多本字典,絕大部分與語言學習有關,包括中文、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記者發現沙發上還有幾本厚厚的英語詞典,問他是否習慣邊看電視、邊查詞典,他爽快回應:「是啊!」
 Adam Makkai教授當年在英文《虎報》撰詩紀念八九民運事件。
Adam Makkai教授當年在英文《虎報》撰詩紀念八九民運事件。
「有時電視播放廣告時段,無興趣收看,所以查字典。小說難追情節,字典有例句,可迅速吸收,又不會打斷思路。」查字典已成為他生活一部分、一個習慣,寫文章遇到某個英文字的意思或用法不肯定時,他就會查字典。用膳或看電視時,也會翻一下,連他的枕邊都有一本《牛津袖珍詞典》,在床上看書也會偶爾翻幾頁。
現實中很少人如他這般耐心細讀印刷字典,他坦言:「文字對我有一種大魔力。」語言學家David Crystal曾以「字彙是語言的珠穆朗瑪峰」為比喻,Jonathan則自喻為文字花園中四處採蜜的蜜蜂,喜歡由一本詞典「飛」(查)到另一本詞典。
他回想初中購買的第一本詞典,是學校書單列明的《牛津高階》(英英)第三版。「當時對字典興趣不大,查完便扔回茶几,整本字典幾乎『內傷』。」中四時,他買了標榜全國第一部以「文法、句型」為編輯要點的台灣《遠流活用英漢辭典》,對他啟發很大。「台灣人出書別具意義,序言寫得生動有趣,原來學語文可以一頁一頁讀下來,一句一句背起來,還引用林肯格言:I will study and get ready, and perhaps my chance will come,很有鼓勵作用。」自此,他對學習英語和寫作更有興趣。
八十年代末,他考入香港浸會學院(現香港浸會大學),主修英國語言及文學,遇上來自匈牙利的英語教授Adam Makkai。「這名傳奇人物出身書香家庭,二十歲時因為蘇聯入侵東歐,逃亡至美國才開始學英文。後來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念書,其中在耶魯修讀博士的論文研究英文idioms,成為權威,大家都稱他idioms man,他很關心學生的。」
Jonathan一直保存教授所送的Th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Idioms(1975),還有一篇英文《虎報》的文章,背後有段故事。「他是感情澎湃的人,雖然在香港的時間短暫,仍然關心社會政治,更寫了一首詩紀念八九民運事件,這是我影印他當年的報道。」
 圖為Adam Makkai於1975年推出的暢銷之作。
圖為Adam Makkai於1975年推出的暢銷之作。
九七前夕的懷舊氣氛濃厚,Jonathan開始正式購買和收藏舊詞典。當年聽說「士丹利街有神州(書店)」(現搬到柴灣),專賣二手書,於是到中環逛一逛,問老闆歐陽生有什麼字典介紹,結果覓得1914年莫文暢編輯的《增廣達辭字典》量訂本,只需350港元。「不能相信1914年在香港出版那麼大型的字典,而且是一人獨力編著,而書名來自《論語》孔子所說的『辭,達而已矣』,即是溝通,最重要能夠表達自己。」
最有趣一次是在西營盤,途經第三街一間廢紙回收店,看見1975年的《遠東英漢大辭典》,正是台灣作家李敖坐牢熟讀的書,在當時華文世界屬最大的辭典,市場上賣四五百港元,他卻以30港元購得心頭好,而且內頁新鮮整潔,是可遇不可求的「收穫」。
Jonathan繼續花時間搜羅新舊字典,可是,舊字典總是「有市無貨」,不是經歷戰亂被摧毀、拋棄,就放在世界各地的大圖書館,加上香港舊書店不多,他有時到摩羅街尋寶,或在旅遊時購買或從網上訂購。有次去到灣仔的三益書店,請教豐富二手書經驗的老闆蕭生,對方在他的筆記上寫了「鄺其照」三字。
1868年,鄺其照是第一個中國人編著英語學習字典《字典集成》,幾年前Jonathan終於在網上找到他的第三版,已改名《華英字典集成》。「這本書要250元美金,本來不捨得買,但是罕有兼屬重要文獻,於是就買了。最珍貴之處是書中有其題字,據說那是他送給朋友Burt時所寫的。」
鄺其照是中國編英語學習字典第一人,論成就,Jonathan卻認為莫文暢最高。「霍恩比(A.S. Hornby)1948年推出的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提出學習英語要注意句型,大受歡迎。但原來在1914年,莫文暢早已強調句型,其《唐字調音英語》亦有助研究香港早期的粵語方言。」
早期香港學英語的華人也受字典影響。「前期學英語的華人分兩類,第一類是買辦、店主或店員、歐籍人士的家僕,他們大都說中國式洋涇濱英語(Chinese pidgin English),從唐字注音的英文會話手冊自學或上課學來的。第二類是正規學校的學童,早期香港的西式學校多由外國教會辦的,英語老師以外國人居多,課本由外國入口,所以學生(包括少年孫中山)學的都是正規英語。當時字典似乎也很受學生重視,尤其是鄺其照《華英字典集成》和譚達軒《華英字典彙集》。另外也有一些專為華人編譯的英語自學書籍,如陸敬科的《英文文法譯述》和羅星流的《英語易讀》。」
1899年商務書館推出的第一本英漢字典《商務書館華英字典》,就以鄺其照《華英字典集成》為藍圖,將兩萬字擴充至四萬字,Jonathan花了250港元在神州書店買到這部經典。「最明顯是清朝流行線裝書,另外因當時中國人自大的心態,英漢字典都叫《華英字典》。」
說字典可以說一整天的Jonathan笑說:「我不想令人覺得我只看字典。」他其實與常人一般會看報章、雜誌,也會兼顧寫論文和家庭生活。「現在查的並非深奧、少用的字,而在閱讀報章看到新的句型而我不明的,就會主動查字典。」
 1899年《商務書館華英字典》(左)以鄺其照《華英字典集成》(右)為藍圖,將兩萬字擴充至四萬字。
1899年《商務書館華英字典》(左)以鄺其照《華英字典集成》(右)為藍圖,將兩萬字擴充至四萬字。
不少歷史名人愛讀字典,林語堂當年眷戀《袖珍牛津英文字典》,讀得不忍釋手,還稱其為「不可須臾離的枕中秘」、「平日消閒最好的讀物」。錢鍾書把《韋氏大詞典》讀三遍,其夫人楊絳更形容他:「重得拿不動的大字典、辭典、百科全書等,他不僅挨着字母逐條細讀,見了新版本,還不嫌其煩地把新條目增補在舊書上。」
Jonathan指,從文獻角度來看,舊詞典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具保存價值。從語言學角度來說,舊詞典記錄了以前文字的面貌,是研究語言變化、語言接觸等大好材料。例如英文「happy in doing something」,這句型在第一本1914年的《英漢詞典》和《牛津高階詞典》第二(1963)、三版(1974)都有列出,但之後的牛津版本已不見了,可見語文隨時代不斷變化。
新朋友及舊朋友
他舉例:「英文yesterday是昨天,來到《牛津高階詞典》第八版增加了形容詞,今天外國人說it's so yesterday,表示很過時。」他認為多學一個新英文字或認識一個已識英文字的新短語或句型,感覺如認識新朋友,或對舊朋友加深了解。
很可惜,現在的學生缺乏耐性,過分依賴補習社老師和互聯網,不肯自修英文,學好基本功,加上一上Yahoo和Google 就有解釋、翻譯連讀音,字典電子化是自然發展趨勢。「傳統印刷字典儲存不方便,而且價錢不菲,書單有也未必會買。」
《牛津英語大辭典》早前宣布停止印刷,只提供付費的網絡電子版,出版社為了經營不得不變身,繼隨詞典配備CD-ROM,提供全文檢查及發音功能,第八版《牛津高階英語詞典》更加入iWriter互動英文寫作軟件,由查詞功能化身寫作工具。
撰文︰林艷虹
攝影︰郭錫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