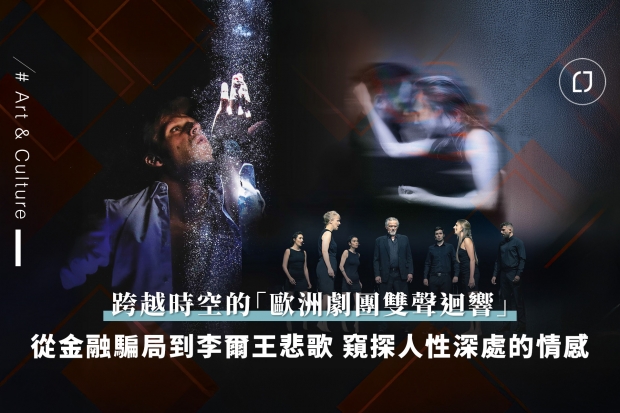Blur封面設計師Julian Opie 倫敦Walking Man踩爆謝菲道
談起Julian Opie總令人想起英國樂隊Blur。這名1958年出生的倫敦藝術家,在公元2000年曾替樂隊設計《Blur:The Best Of》唱片封面,那簡約線條配高明度色彩,單點眼睛,早已深入民心。這也是一貫Julian Opie畫風。近年,Julian Opie一直用擅長畫風做大型Public Art,做Walking Man。他筆下的Walking Man走過都柏林,走到日本,近日更應邀替Tower 535做永久性作品,四個倫敦人走到銅鑼灣謝菲道。
早前Julian Opie來港創作時,LJ跟他做了一個詳細訪問。
文:何兆彬
LJ:Lifestyle Journal
JO:Julian Opie

 《Blur:The Best Of》
《Blur:The Best Of》

四個倫敦人
LJ:可否解釋一下近作Tower 535作品"Walking in Hong Kong"(在香港步行)的緣起?又談談當中的構思元素?
JO:人們常以為藝術家、音樂家會突然有靈感,想起一些構思,但其實不是這樣的。所有人工作時都有一個系統,
一個過程,一天一天的把它累積。這當中有些想法我由一開始就開始做,已經做了三十年了,逐步建立了這些繪畫
、這些想法、看待這世界的角度。所以"Walking in Hong Kong"這作品其實是我打算做五年的一個系列作品之一。大概五年前,東京有人找過替一座新建築物的大堂做雕像,我受到一個韓國的士司機的車頭LED燈──上面有一隻賽馬顯示你花了幾錢的這觀念啟發,它看來像商標,混合了自然及生命、金錢及當代科技,看起來就像一幅小小的美麗繪晝,所以我把它結合了雕像,然後我想:啊,我是否能做一個行人,由一處行到另一處呢?
我做了一個在St. Louis,當地記者計算過這人仔能行多遠,而結果是他可能已能圍繞地球一周了。當地完成時我
們舉辦過一個小小派對,那是2,500公里遠。他步速一致,就像水流一樣,所以很好計算,當我獲邀替Tower 535做這計劃時,我不是馬上想起LED步行人的,我手上有很多工作同時進行中,而當我看看Tower 535,它的優點及缺點,它只有三面,它的角落是不規則的,Tower 535需要的熒幕不是平常一直用的大小,我得來香港,拍下好多影片,用電腦算一算,才找到最佳方法。
結果我畫了四個人,大廈的每一面有一人,你可想像,當我想將大廈變成一個整體,像遠古埃及的巨像一樣,我要
用這方法去想像,才能令你個人繞著大廈走。他們走得不快,其實算是慢的。
LJ:這四人是怎麼找來的呢?
OJ:我在倫敦街上找的,我太太在街上見到適合的人就問他:「不好意思,你能來我們工作室嗎?我會給你五百港元作報酬,你簽一張紙,而藝術家就會把你畫下來。」我工作室外開始排了一條隊,我想有三十人來過吧,衣衫都沒變,他們走上步行機上,不斷的行,我以高像素菲林、普通菲林雙倍速拍下,然後我用手一格一格的畫,大概是每一條片用上一百張繪畫吧。當你將他由頭放到尾,再回頭放,它就成了一個循環(Loop),就像人走路一樣。
最後用上在Tower 535的四個人分別是:
Daniele:她看來像個侍應,或生意人,她身穿大衣、白襯衫,頭髮綁得高高的。
Luca:他是個酒商,個子很大,他是意大利人,我想他一定熱愛生命吧。
Shahida:她較像一個有型學生,大概是在這區做設計的吧。我工作室這一區都是設計及藝術工作室、Cafe及夜店
。
Fame:有型男士。他身穿迷彩軍褲,Tee、短髮。
我們手上就用這四個人,我把他們轉到這裡,他們不知道自己被移送到這裡呢。但他們簽了紙呢。


永久性作品
LJ:選擇這四人代表香港,當中可有原因嗎?
JO:有的,我跟兩個動畫師工作,所以一共是三人,我畫了原畫,他們再照我畫的完成。
我們首先畫的是朋友及家人,或工作室任何人。第二組人是我們在街上用長鏡頭攝影機偷錄的行人,技術上這有點
困難,他們身上有袋有耳機、及手機。再下一組人,是慢跑的,我喜歡這組,因為人一跑起來就好似動物,動作很
美,比步行美得多了。然後我想再要一組人,我很小心,因為我已學了不少,新一組人有十二人,一半男一半女,
我嘗試平衡一點。
為了Tower 535我選的人都做簡單動作,因為解析率太低了,它不可能表達出複雜動作。這組作品比它身邊的東西
都要低調得多。Tower 535上沒有廣告,沒有顏色。我常常把自己的作品放入廣告堆中,接近人群,接近商舖,我
也設計唱片封面、Tee、繪畫、LED熒幕,我不認為藝術是一定要放在藝廊或博物館。
我們花了好多時間做公共藝術裝置,這不容易,你知道你得要有份合約,很複雜的。我會說有一半機會當人問你有
甚麼念頭時你一無所獲,這是我第二次為香港工作,但第一次的作品已消失了。變成了Tower 535的作品才是我技
術上第一個在香港的作品,而且是永久性的作品。
LJ:所以“Walking in Hong Kong”這作品會是一件永久性作品?
OJ:對。
我開始工作時是八十年代,在日本,我又有韓國首爾有一所藝廊,來到香港很刺激。發展商把大廈變成一座雕像,
這一舉十分之勇敢。
LJ:“Walking in Hong Kong”這計劃做了多久?
OJ:由當初議計大概有兩年吧,最初的建議不是這個想法的,那個構思只在低樓層及高座出現,細小好多。一個月
後發展商再問我有何建議,最後我們決定用大熒幕,對此我很高興。
構思是每一晚,只在晚上,會有兩個小時──也許是這兩小時是分開的,一個鐘,然後夜一點再一個鐘播放。
Tower 535上的作品是永久的,在晚上看來特別好,它比我想中更好,不管你在橋上、在酒店、在餐廳效果都不錯
,就算是在大半里外看,一樣看得明白。當然,這影像對香港人來說是相當大的,我也曾因為它的大小而多少有點
害羞它。
沒有密碼
LJ:在它那抽象風格背後,你是否有甚麼訊息想說呢?
OJ:我不會把它稱為抽象風格,我經常以代表到現實為創作目標,現實是不容易創作的一件事,我們有相片,相片
是真實,但同時是平面及死板的,它不像我們現實中的生活,充滿了情感及三維。一張這房間的照片,不能代表這
房間,現實比這個複雜得多。我了解它們的方法,是我用符號去代表人們,而我一直在尋找繪畫的方法,你可以畫
得像米高安哲羅,或梵谷,重要的是你要建立一套自己的語言。我從小就不斷的畫,不斷的看,把我自身的經驗去
畫點東西出來,我一直畫,但我沒有政治訊息,它不會是你看看這作品,然後知道下次要投票給誰,對很多藝術家
來說,很重要的是你作品中不要有密碼,有一些規則的,例如更開放去看現在在發生些甚麼,去做實驗。
我不知道把這些人放到大廈上,會發生何事,它像個實驗,像煮菜一樣,一點這個汁,一點肉,慢慢你就建立了一
些東西。有時它會很可怕的,但有時它會慢慢發展得比你想像中好,然後你用它去發展出另一些東西,藝術創作好
多時就像烹飪,畫一畫,看一看,再了解我們的存在。
LJ:這計劃的挑戰性在那裡?
OJ:如果我想說得有趣一點,我該說最大的挑戰是那合約。當你始寫下規條,它會變得十分複雜,而律師又變得很
緊張。二十年後會怎樣呢?最好是這麼說吧:我很好,你很好,我們都盡力吧。這是一張較好的合約,因為人人都
想要最好的解決方案。
藝術上看,最大的挑戰是環境的複雜性,這大廈不是到四周可見的,只有一些角度會看得清晰,到了最後,它遠遠
看起來──即使是由海港看過來,也比我想像中更清晰,跟我原先構思也有增添了一些角度。
LJ:人物都由右走向左,當中可有意思?
OJ:當我在九龍,我跟我助手說:也許我們應該把人反過來走。對我來說,它就像文字走動一樣,而我們習慣由左
看到右嘛,我知道有些國家是反過來的,但我仍然認為大家是這樣閱讀的,所以也傾向這樣做了,原片是由右到左
的。


LJ:你怎看香港的公共藝術圈子?
JO:在英國,我有個朋友是經營博物館的,他說最好的公共藝術,就是樹木。如果你想對大家好,你種一顆樹吧,我明白他的意思,誰要公共藝術了?我們喜歡公園及樹木,或許再加一點有趣的給小孩,但公眾藝術對大家在外享受它,是有點困難的,由於你在大自然裡時,大自然會比藝術更好,沒甚麼能比大海、高山相比的,所以,就別去試嘛,由大自然自己就好了。
縱使這麼說,我也做過一些公園雕塑,人們喜歡做公園雕塑。對我來說,在城市工作是要好一點的,因為你擁有這一套繁忙的視覺語言,而當我把作品一放下,我覺得就像回到家裡一樣。他讓人暫時離開廣告,離開資訊,離開店舖,離開大廈,擁有一個全然屬於自己的瞬間。要做公共藝術是很難的,因為沒有人要求去做,這大廈後面也許會有人想要,但沒有人問過我,它就像你在沙灘上有個收音機,在你旁人人都會「呀」一聲,好像即使它播的歌是你喜歡的,你也覺得它討厭,因為歌不是我揀的嘛!所以這問題不簡單,做不做公共藝術好?它不像是問你藝廊或博物館哦,如果你做一個藝廊展覽,你做甚麼都可以,我可以做一些「哽」一點的作品,因為來看的人是想來看我的,但公共藝術不一樣嘛,你一定要有禮、更小心,所以我開始思考:怎樣會有趣一點呢?怎樣會又有趣味,又不太掗??每次我做公共藝術,我都會問自己。
在倫敦,從以前──十八十九世紀,我們就有好多公共藝術,它們以銅製成,也許題材是著名政治家、戰爭中歷史人物,當你在倫敦有這些雕像,就好像這個城是住滿這些士兵和政治家一樣,我以為人類經常會這麼做,你在希臘古城、埃及城填都會見到,他們把建築混合人的影像,通常都很巨型的,人類很自然就會在中間做一個連繫,它叫「神人同形同性論/擬人化」(anthropomorphizing),就像在卡通之中,桌子是能說話的,或有人面,人類常把自己的情感、人性放入環境之中,我們這麼做去接通世界,繪畫或雕塑、雕像、建築就是我們把人性及建築物的物料及現實轉化的方法。
LJ:你怎看香港藝術圈?
JO:我只來過香港三次,所以沒有專業意見去評論。我會說若你有一個好的藝術圈,你是不能由頂往下壓的,你可以把將事情最大化,但一個真正好的藝術圈,它需要由藝術家中而來的,你要有藝術學校、藝廊、從地而起的能量,但當聽到酒店說香港甚至沒有一家當代藝術館時,我很不開心。這就是說,將來有更多藝術博物館會開啟,香港視覺很強烈,你在街中就見到了,香港有這種視覺文化。
你們也有世界知名的藝術展,人人都知道香港的Art Show,很多跟我合作的世界藝廊都表達了希望在香港Art Show展示作品的慾望,我們必須要小心把作品分享到韓國、倫敦、柏林等地的藝廊,對大家來說,香港是亞洲之窗,也許你已收到消息,很多世界知名的藝術專家都會來香港出席藝術展,雖然對專家來說(不是對大眾來說),受博物館及藝廊重用,仍然是強大及重要,例如,去在博物館/藝廊辦一個展覽就是一個想法,因為這會吸引更多人去看。
LJ:你喜歡世界那些地方?
JO:我在英國近海有一橦房子(House),我很喜歡留在那裡。英國不怎熱,我們有一艘小船,經水路可到小村莊,那是我祖先從前的住處,那裡近海,從前還有些礦工,但後來都去了澳洲,因為英國沒甚麼礦可挖了,所以他們去了澳洲挖,後來我父親回國了,這是我的根所在之地。由這裡去倫敦,路途遙遠,但我們還是常去的。我做過很多關於這地方的作品,有船有海也有鳥。若你上我網站,會見到它們的。
LJ:你的作品常展示人們在現代城市的生活,但你喜歡寧靜的環境?
JO:我的作品受兩者影響,我在寧靜中做過不少作品,例如在廟中,我也喜歡倫敦。我在倫敦住了多年,也經常出出入入,這是個偉大的城市,充滿靈感,它比你們的香港要多一點空間,我在那邊有兩個房子,倫敦也有很多公園,會令你感到空間太一點的。它通常很冷,這不大好,但我們也有很多好的博物館及很有活力的文化,我沒有慾望搬到?一個地方去工作呢。
我喜歡旅遊,但我沒有一個國家是特別喜愛的。去看及去學習不同國家文化永遠是好的,作為藝術家,去到不同國家,去創作,這經驗是神奇的,若你以旅客身份去訪一個國家,那也不錯:有餐廳有沙??有博物館,也有人群及酒店。但當你去工作,你會去本地的地方,去認識人,去到世界的另一面,這比較真實。縱使這麼說,我還是不喜歡在工作中去太多旅遊,因為我不能選擇去的地方嘛,我會想去大溪地,但沒有人邀請我去做公共藝術呢,所以我去了首爾、柏林、紐約等地,這些有藝術圈的地方。我很喜歡羅馬,那裡有很多古羅馬城鎮,你會見到神奇的文藝復興皇宮,也見到1930年的美妙建築,那裡還有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在羅馬有一所小小的藝廊,我也常去那裡工作。
LJ:你下一個計劃是甚麼?
OJ:我在全世界約擁有12-13家藝廊,而每3-4年我會舉辦一個展覽,期間我會出席藝術展或做委約作品,我也畫肖象,每三、四年會在藝廊舉辦一個展覽。
我下一個計劃,是六月在維也納展出「面孔」,那些繪畫上只有人頭,人們不會動。展出的只有畫、雕塑。十月一日我會有一個類似的展覽,在日本東京,然後我會去上海談一些新計劃。2018年我會在澳洲墨爾本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它類似是倫敦Tate Modern)有一個大型展覽,我正在收集一些想法,因為現在距展覽只有兩年。
我還有一個攝影展在倫敦,我會把人帶到工作室,有一名攝影師,我會要求被攝者坐著、站者擺甫士,拍下好多相片。她(被攝者)需要來幾星期拍攝吧。
這星期我也會開始創作一些風景作品。
LJ:會有突破性的創作嗎?
OJ:突破聽來不錯,我覺得Tower 535對我來說是個小小突破,我也在首爾做了一個好大的作品,在一個大建築物上,它是平面的,只在其中一面展示,每次展出約20分鐘。
而Tower 535令我覺得它像一個大型雕像,因為它是四面的,它會展示相當久,你可以把它當是一面鏡子,看完再看。這對我來說是新鮮的,昨夜,我走過銅鑼灣,在希慎吃飯,看看我的作品,我覺得它真是新鮮而且令人感到刺激的。
我想,每個作品都是一個小突破吧,因為你必須令它成功,你一直在試,若然不行,它令你掙扎,但可行的話就是小突破了。
Tower 535地址:
銅鑼灣謝斐道535號
(暫定播放時間為每晚7:30pm至9:30pm,但日後會更改)
(編按:Tower 535位置在銅鑼灣謝菲道,總統戲院再往東行一個街口。據上面Julian Opie說,在希慎吃飯也能清晰見到,但未知他所知是那家食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