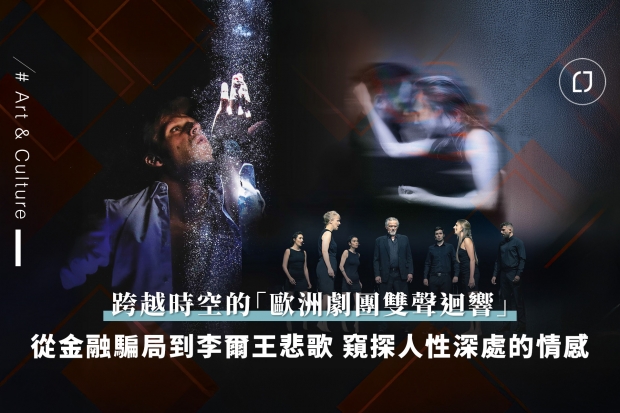台灣攝影師劉振祥 下指令的人
 雲門 @ 池上《天光.霞》
雲門 @ 池上《天光.霞》
每年十月尾,台東池上的稻穗之間都放置了舞台,展開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今年的池上秋收再次請來雲門舞集演出,門票幾秒就被搶光了。雲門與池上關係密切,每幾年就來演出,與從前不同是今年林懷民退休了,由新任藝術總監鄭宗龍接任。不變的是,雲門成立36年來,替他們拍攝造型或演出照的都是劉振祥。祥哥是台灣著名攝影師,他拍表演藝術,也拍電影劇照師。他與池上關係匪淺,2021年疫情期間他應邀來池上當駐村藝術家,替這裡創作出一幅幅詩意又動人的作品。祥哥說無論AI又好,科技怎變都好,始終攝影師才是下指令的人。
TEXT & PHOTO BY 何兆彬(PORTRAIT)
(演出照片由台灣好基金會及劉振祥提供)

池上的航拍
2009年,池上人在秋收前割了一小塊稻田,讓基金會放上鋼琴,由陳冠宇在此彈奏,當年的演出規模較小,但綠田上彈鋼琴的照片一出來,在網上傳遍世界各地。11年林懷民來到池上,開始了跟藝術節討論演出,2013年的「稻禾意象 / 雲門選粹」,他早一年就先找了祥哥來到池上做準備。祥哥憶述:「所以我才來到池上,那時候觀光客也不多,來了我才發現這裡居然這麼美!以前我們常常去台東,只是路過,都沒有真正停下來,直到那一次我才真正認識到池上原來這麼美。」演出成功,雲門每隔幾年就來一次。自此祥哥與池上結緣,2021年疫情期間,他應邀來池上當駐村藝術家,用航拍拍下一幀幀詩意的作品。
「航拍這個東西,面對的都是很大的景觀。人站在地面的時候,看到的可能就是一小塊田,但在天空往下望,人小到幾乎是看不到,人走過的痕跡,器具劃破土地的景觀,我們從地面是看不到的,因為我們太渺小了。只有用那麼高的視角,才能夠看到整個土地的變化。」這些航拍照一點也不像他平常的攝影風格。祥哥把畫面當畫布,農田上機器拉過的痕迹當是筆觸,池上的梯田當成是色塊,他拍攝生涯數十年,總是一直在尋找新的視角,「我很喜歡嘗試各種不同的一個視角,每一個地方,可能一些人覺得好無聊,我會從裡面再去找到一些可能性。」
 2021 年疫情期間做池上駐村藝術家,用航拍創作。
2021 年疫情期間做池上駐村藝術家,用航拍創作。
鄭宗龍的舞更難拍
喜歡嘗新,他也不怕重複。跟雲門舞集已合作了36年,同一支舞,拍完又拍,「昨天演的《天光.霞》只拍了第二次。」《天光.霞》海報上的攝影,其實只是他在記者會舞者綵排時拍的,不是專門拍的,「當天很多媒體採訪,我也在現場拍。而且當天我是替兩廳院拍,不是幫雲門拍,但他們看到了喜歡,就跟兩廳院借了照片來用。當天記者雲集,按理說人人拍的都差不多,但他總是有辦法拍出新意,「(拍表演)有經驗的話,很好掌握,你知道舞者的動態其實不難。他們跳的話,基本上都可以掌握,只怕他們不跳。」
但剛好,鄭宗龍編的《天光.霞》跳動就很少,「其實他跳很少,他是在玩結構變化,兩個舞者身體互動裡頭展現線條,而線條是糾葛的,展示上有難度。通常跳起來比較好抓。」如果問世界上最了解雲門由林懷民換上鄭宗龍,兩人在編舞上風格的差異,祥哥一定是其中一人,「兩人差異非常大。林老師的舞作比較傳統,他會盡量的讓舞者展現平衡的規則性,尤其2018年《松煙》超級的美!因為他是很規則的,每一次結構變化都非常完美,舞者的關係、動作,會跟田形成一幅畫。可是鄭宗龍一直在打破這個東西,他不要落入傳統的舞蹈裡面,平衡和諧那些他都不要。」祥哥笑說:「鄭宗龍的舞者很難過,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盡情的去伸展!一直扭在裡頭。」對攝影師來說,當林懷民的作品出現和諧結構,他就按下快門,但鄭宗龍不能這樣拍,「應該說, 鄭宗龍的東西比較難拍!他故意去破這個東西,所以我必須在舞裡找到一個視覺平衡,背景跟人物的和諧。他作品裡面很多雙人舞,很多動作都是沒有丟出去又把它扭回來,不斷糾葛。」拍攝上,有時候他選擇拍特寫,刻意用背後的山做呼應。
 為《大佛普拉斯》拍劇照,這張成了外國影展的主視覺。
為《大佛普拉斯》拍劇照,這張成了外國影展的主視覺。
林懷民始終如一
合作多年,祥哥說林懷民性子沒有變過,對美的要求從來都很嚴格,「他對美的要求沒有變過,就是不斷的追加,對事情的要求沒有妥協,始終如一。」有曾替林懷民工作的朋友說,有次他在台上工作,用膠帶在地上貼了一個個十字以讓大家辨認位置,台下觀眾是看不見十字的,但林懷民見到馬上叫他撕掉,因為貼得實在太醜了,祥哥深有同感,他笑:「我們拍照的時候,他會叫技術人員把所有的Mark全部都拆掉,技術人員不想拆,因為那個貼那個尺寸要量很久。他就是每一個細節都有要求,要求非常非常的嚴苛。」但祥哥說,自己算是雲門外聘的人,老師對外人總是比較寛鬆客氣,如果是雲門裡面,要求就更嚴謹了。
祥哥本是攝影記者,小時候讀復興商工美術科,1986年進入《時報新聞周刊》,曾有七年時間做攝影記者。台灣87年解嚴,不同的聲音陸續出來,社會爭議不斷,運動一直升溫,整個社會十分燥動。他一邊拍新聞,87年同時開始拍雲門,「新聞的東西很直覺,都是瞬間的,有時候遊行抗爭隊伍走的時候,忽然間爆發什麼事情你就要趕過去。」他目睹整個社會變化,記憶猶新,「解嚴以後,一直到1992年社會才算是過度過和平的轉換過程,因為後來還要修法。修法都是抗爭出來的,由很多人的力量去推動,是社運人士不斷跟警察對抗,政府才去修。當時我都在現場,情況跟前幾年香港一樣,每天到處都發生事情,一發生事情我就趕過去,很難忘!」他說,最棒的一點就是說見證了一個大時代的轉變:「它是近代最大的民主化過程,台灣本來被外來政權(日本)所控制殖民,一個政權(國民黨)來了,一夜之間國旗通通撤下來要換了,明天開始不講日語,要開始講北京話。那種過程,經歷一個個反轉。1989年鄭南榕自焚,90年李登輝跟郝柏村在競爭,把他把軍人變成行政院長,剝奪他的軍權,到了1992年衝突最嚴重。」當年台灣廢除「刑法一百條」,此法規定「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着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此法一廢,祥哥知道台灣今後有真正的言論自己,就辭職開自己公司了,「有言論自由的地方,你講錯話沒有人會把你抓去關。93年以後,我自己出來成立工作室,接很多案子。」他看準了社會一自由,不論文藝創作、廣告什麼都會旺盛,那段日子他幾乎什麼都拍過,表演藝術拍!藝術文化拍!模特兒時裝照他也拍,連拍賣行古懂圖錄他都拍過。有些東西之前沒有嘗試,那就邊做邊學。
 1990 年野百合運動在中正紀念堂拍下這一張,如今掛在常設展,代替了蔣公的肖象。
1990 年野百合運動在中正紀念堂拍下這一張,如今掛在常設展,代替了蔣公的肖象。
拍劇照好玩
86年進入報社,但前一年他就開始替侯孝賢《戀戀風塵》拍劇照,同年又拍了楊德昌《恐怖份子》。到了替報社工作,就有22年沒有參與過電影劇照了,直至2008年鍾孟宏找他,祥哥又回到電影裡面。他的拍法跟一般劇照師不同,別人都現場拍攝時安安靜靜的拍,他卻往往在叫Action之前或Cut之後拍下一張張動人照片,事後都被導演拿來當劇照使用,《戀戀風塵》他拍的黑白照,加上顏色變成海報,2017年《大佛普拉斯》參加外國展覽的主視覺中,菜脯(莊益增)在大佛仍未安裝頭部,跑到裡面,把頭伸出來的的影像,是祥哥在現場見到有工人曾跑到佛像裡,他覺得很特別,另外叫了演員進去拍的,電影裡根本沒有這一幕。事實上,鍾孟宏找他來拍攝,也是由於他想要祥哥的創意,若要電影裡出現的畫面,用電腦擷取就可以了。重新回到電影現場,他拍得十分高興,雖然電影拍攝收入不高,工時又長,但實在很好玩,「有時間我都會接。拍電影用工時來講很划不來,但它提供一個條件。我跟鍾孟宏拍第一部片子《停車》我們就跑到東北去,那個地方我從來沒去過,他們租了一台火車在田裡開,那就很過癮!」
拍了這麼多年,攝影由底片變數碼,如今又有人工智能的出現,它的定義一直在改變,那到底攝影是什麼?「AI那些東西都沒關係,還是再回到初心,你AI可以幫你生成,可是你也要懂得下指令。其實攝影師就是下指令的人,主控權還是回到攝影師的眼睛,他怎麼樣去詮釋畫面。尤其像新聞攝影,現場那麼多人,那麼混亂,你站對位置很重要。我的照片是安靜,是凝視的,這是很多人拍新聞的人最欠缺的。」
他舉了個例子,1990年祥哥在中正紀念堂拍下當年野百合運動,萬人聚集,「我拍的群眾運動,前面一個人的背影最大,正面全部都是人。文化部看到這照片得很適合,它現在是常設展,在中正紀念堂二樓展出,從前這裡是八米的巨型蔣介石、孫中山的肖像,現在換成了我的照片(群眾)!」
 2008 年回到電影界,為鍾孟宏拍《停車》
2008 年回到電影界,為鍾孟宏拍《停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