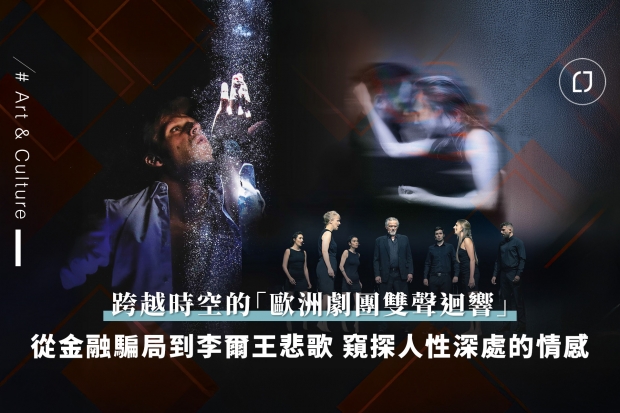占飛:我仍然能夠講一聲:我係我?
1976年,黃霑為電影《跳灰》的主題曲《問我》填歌詞,裏面有一段相信不少香港人都能唱出來:「願我一生去到終結,無論歷盡幾許風波,我仍然能夠講一聲:我係我。」很顯淺的歌詞,意義卻不顯淺:二戰前後出生的一代港人,已經由傳統過渡至現代。
純看字面的意思,「我係我」不過是邏輯的同一律,即A是A,並沒有說出任何道理。然而,從中國傳統文化去看,中國人呱呱墮地,就不單是獨立超然的「我」,而是活在家、國的網絡中。
我是中國人,就有「責任」愛國;我是父母的子女,就有「責任」聽話;我是哥姊,就有「責任」愛護及提攜弟妹,反過來,我是弟妹,就要尊敬我哥姊。我是家族一分子,就有「責任」光宗耀祖。我是社會一分子,就有「責任」做個有用的人,回饋社會……這些「責任」,我是逃不了的。
現今許多中產父母,還要子女「贏在起跑線」,兩三歲便安排了子女的學習和生活,子女有「責任」遵照父母的期望,入讀名校小學、中學、大學,之後找一份高薪厚職,晉身「人生勝利組」。
 個人主義如今已近乎天經地義,但消費和媒介不斷「操弄」個人的偏好和思想,大眾往往隨波逐流,許多人有的只是被「操弄」的虛假自我。
個人主義如今已近乎天經地義,但消費和媒介不斷「操弄」個人的偏好和思想,大眾往往隨波逐流,許多人有的只是被「操弄」的虛假自我。
究竟子女的「我」,是父母鋪排的「我」?還是孩子自己想要的「我」呢?究竟這是父母希望子女過的人生?還是孩子想要過的人生呢?如此「一生去到終結」,孩子能否「仍然能夠講一聲:我係我」呢?父母倒是不管的,父母亟亟於成就的是子女的「幸福」,而所謂「幸福」,卻是按照父母的標準釐定的,通常都是健康、事業、社會地位、財富、家庭等等世俗之物。假若子女追求的「理想」可能危及上述「幸福」的定義,例如出家為僧,恐怕大多數中國人父母口裏不說,內心都不會同意或支持的,頂多說:仔/女大仔/女世界,隨他/她去吧!
「我係我」背後是個人主義。西方文化遠比中國文化更早提倡個人主義。西方思想史上首位有姓有名的思想家,公元前七世紀的古希臘人泰勒斯(Thales)便說過:人最難的是認識自己。相傳德爾斐(Delphi)的阿波羅神廟,刻了三句箴言(Maxims),最為後世熟悉的便是:「認識自己」。蘇格拉底曾說:「未經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他說的「省」,便是「認識自己」。用什麼去「省」、「認識自己」?用的是理性。「認識自己」,才能知道我是順從自己的真正意願而活,還是順着父母的期望和社會的習慣而活!
不能保存真的我
儒家也重視「省」,但重點不在理性的「省」,而是道德的「省」。曾子每日「三省吾身」,是「省」自己與人謀有沒有不忠誠?有沒有與朋友交往而不信?傳不習?這也可以說是「認識自己」,但主要是認識自己的行為有沒有違反道德,有沒有遵從儒家的標尺待人處事。蘇格拉底主張的認識自己,卻是了解自己的性情、才能和愛好,以訂立理想,追求個人的完成。他的徒孫亞里士多德主張,人要追求幸福,必須兼顧家庭、朋友、公義……但最後目的依然是個人的自我實現,而個人必須自由、自主、自決和自足,才可實現自我。
這便是西方的個人主義,也是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古希臘大哲明白,若個人主義偏差了,會流於自我中心,自大、自私及自戀,是以古希臘有水仙花的神話,警惕世人不可自戀,自戀並不是真正的個人主義。中世紀的基督宗教,順着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的思路,提出人生在世的理想,乃是崇敬上主,遵守誡命,博愛行善,所為的是個人的救贖,死後上天堂,而非光宗耀祖。
隨着資本主義興起,個人自由增加,宗教及教會的影響力縮退,一方面個人主義如今已近乎天經地義,不言而喻的信念,另一方面消費和媒介不斷「操弄」個人的偏好和思想,大眾往往隨波逐流,許多人有的只是「不真誠的自我」(Inauthentic Self),被「操弄」的虛假自我。《問我》一曲結束時有這樣的歌詞:「面對世界一切,那怕會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正說出現代人的夢魘:現代人終生營營役役,卻不能「保存真的我」,甚至未能認識「真的我」!
撰文:占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