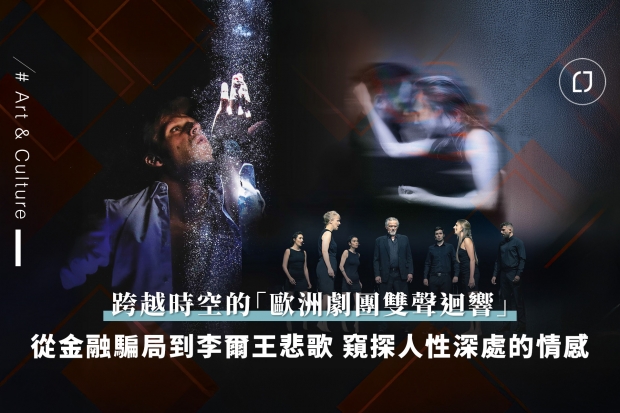【立體的探索】燒掉回憶 永久保存
 陶藝藝術家謝淑婷(Sara)
陶藝藝術家謝淑婷(Sara) Attire衫(2002)
Attire衫(2002)
TEXT AND PHOTO BY 何兆彬(部分相片由藝術家提供)
分手的故事
分手故事,記者記錯是失戀故事,「不是失戀,其實是我背叛了……」Sara 輕聲說,「我由12歲認識他,大家由中二開始是同學,中七拍拖,到我入了藝術系他讀理科,大家完全好唔同,他做了他的專業,正正是因為兩個人越行越遠……分手我比較內疚,他內向,朋友不多,我在他的世界裡佔比較大。」
那男孩追了她好多年,她後來接受,只是出於偶然,「因為我們住青衣,有次要一起考 Oral 口試,卻遇上爆水渠,他為了等我考試遲到了一小時,我很內疚,才跟他一起。」所以原來也沒有怎喜歡他,只是成了情侶後即使性格迥異,「認識太久了,中學的回憶,大家去哪裡,例如去意大利也是跟他去的。」Sara 的工作室全堆滿了舊物,幻燈片投影機有十多部,桌上放滿一叠叠舊照片,其中一些 3R、一些 2R,已經發黃。Sara 說自己超級感性,而她的創作,都與舊人舊物,回憶有關。
這些回憶,全都承載在舊物和回憶之中,後來Sara的創作路上,決定把它們燒成作品,封印回憶,也是出於偶然和嘗試。
「中大畢業後我去了日本做陶藝交流,他們的手藝好好,大家都做碗碗碟碟。我在中大的教育背景受陳生(陳育強)教育,我會想如果是我做會怎做呢?是否整個陶瓷界都只做碗碟?」她憶述,當年的陶瓷界沒有人做裝置,即使做雕塑類,也是有個底座,安安份份的放在上面展出。
家姐是我偶像
日本之行後,1999年她得陶藝獎,獎項是樂天陶社給予每月$3,000資助,另外可使用他們場內的所有設備。當時 Sara 剛大學畢業,在中學當了兩年老師,她白天上班,晚上去陶社練習,「因為覺得自己技術也不是很好。」當老師很忙,除了美術還要做班主任,教中文,「一星期改80篇文,40篇周記,很忙的。」
1999年她舉辦第一個個展 Pottermaid,展出的是一塊塊的「陶磚」,概念來自拉胚時人的右腳要踩腳踏,左腳需要墊一塊紅磚,以作平衡,「我做這個有點諷刺意味,因為它要追求絕對的角度平衡,因此我把場刊做成產品目錄一樣。」她諷刺傳統陶藝都做杯杯碟碟,幾乎像工場一樣,大量生產。她喜歡陶瓷,但可不想走上同一條路,但這展覽沒有受到什麼注意。
為何選陶瓷?「讀中大陳生給我的分數很低,通常是 B-,但我做陶瓷分數高,有 A-。」Sara爽朗的笑:「也許我該多發展這一邊,這是際遇。」那你喜歡陶瓷本身嗎?「我鍾意的,對我來說比畫畫容易,而且我畢業後去日本看到世界是這樣,發現它是可以發展的,當時沒有人做當代陶瓷。」
回到那分手故事上,中大畢業時,她花了兩萬多元,做了一條樓梯裝置展出,「當時是窮苦學生,做好展完要拆掉,但你是藝術系學生,當然拼盡,藝術幾乎是自己的生命全部嘛!就把概念實行然後毀滅,只留下幻燈片。前男友覺得我浪費金錢,因為我存了六萬元這樣花掉二萬。當時他跟我借錢去炒股票,但結果又賺了。」世界荒謬,與她價值觀不符,令她困惑。
做老師非她志向,她想進修。Sara 的家姐是著名藝術家謝淑妮,「家姐是我偶像」,當時比她大六年的姐姐已在美國大學教授藝術,於是計劃到美國升學。
火炭工廈
「我辭了職,先去了美國一趟,回來卻發現母親不認得我,她患上老人癡呆症了。由於沒有人照顧她,就留下來了。」本想到美國升學,甚至想過去了未必回港,Sara 前男友卻跟她說待她畢業就在天水圍買樓結婚,她笑:「我心想,就算要住也住長洲吧。」去美國本有逃避現實的意味,去不成,更添分手決心。分了手她早上照顧母親、創作作品,下午放課後到中學小學教陶瓷班,同時讀澳洲的 MIRT 的藝術項士課程。
「做老師時我存了一筆錢,反正不去美國,跟朋友夾錢租了工作室。」沙士前她見樓價大跌,遇上一個30萬的工廈銀主盤,就把它買下來,後來沙士肆虐,她教的班都停了,她就躲起來天天創作。
《衫》這系列的創作靈感,也有點偶然,「有一天我在抹枱,發現沾滿白瓷泥的布都硬了。我心想若把它燒了會變怎樣呢?這是實驗,結果衫從窰裡出來,發現美極了,開始大規模創作,我開始什麼都拿來燒,公仔麵又燒,煎堆又燒。」沙士期間,她發現工廈鄰居專收舊衣,門前堆積的舊衣中,隱約見到七十年代舊式嬰兒孭帶,「裡面有好多故事,到底是誰穿過呢?我不敢碰別人的舊衣,就拿了自己的開始做起。」
這些作品,都跟(燒掉的)物件本身有關。《衫》的出發點是於她想忘記那段舊情,她發現物件進窰後一燒,衫燒掉了,只餘它的外形。喜愛儲舊物的她,一度想將跟前男友相關的衣物隨記憶全都燒去,後來才發現燒掉外形,但那段回憶反而被定格了,永遠存在。
新搬進火炭工廈單位時沒水沒電,Sara 取水時碰到藝術家呂振光,才發現大家是同幢大廈鄰居。呂是資深藝術家/藝術老師,建議大家在工作室搞展覽,呼朋喚友,前來參觀,結果最早期的火炭藝術工作室展覽就此展開,「展出時有一個女士來看,說很喜歡我的作品,她說想要收藏的就是那批『衫』,原來她是香港藝術館朱錦鸞館長。」
小小展覽只有幾天,卻改變了她的命途,「之前做展覽仆到直,沒有人看,也沒有人寫。初到火炭我完全不知道有人在做藝術,之後搞展覽,來的人也很少,但質素很高。是因為那次藝術館購藏,才令我覺得,咦,原來會被賞識,它們不是垃圾來啊,哈哈!」
母親的回憶
Sara 從來沒有喜歡過繪畫,總覺得繪畫好難,「小時候我喜歡在沙灘撿些沙回來,自己用白膠漿勾出線條,這樣創作。」這不就是多媒體創作嗎?「我做好多手工,但我以前選的東西與自己有點距離,總是冷冰冰的,到了開始用自己的衣服創作,我開始得心應手了,因為用了自己內心的東西,而且有好多發揮。」
她早期的《衫》都是摺起來的,沒打開,燒好後更打不開,「像放了好多秘密在裡面,埋藏了好多故事,幾時穿過,穿了見誰,最初我以為這樣會忘記,但它永遠留低了,像把一件事情了結,但其實了結不到。」這些作品大都是白色的,因為她喜愛白瓷泥。她工作室有一件淺綠色的作品,Sara解釋,由於衫成份中有金屬,燒過後就會呈現綠色。
工作室堆滿舊物的她,創作都與回憶有關,把故事封存起來,用創作轉化,就不再害怕忘記,「最初我用自己的衫創作,之後我用母親的衫,因為她善忘嘛。後來她病情很嚴重,連我都忘記了。」
她清楚記得,母親告訴她自己是馬來西亞華僑,因為其父母太思鄉,帶她回祖國建設,但及後馬國又擔心她是共產間諜,不再讓她回國,謝母輾轉到了香港,認識了 Sara 父親,「我認識這世界從父母開始,她談的都是記憶,她小時候的事情。」以母親的舊物做作品,她說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自己在疾病上幫不上忙,「但我會有盼望,有這個動力,也會釋懷,例如拿着她的舊物,會透過作品去思考她這個人。」創作對她來說完全是自愈,「救完自己,如果你也有共鳴就更好。」
救自己的這些作品,獲幾家博物館收藏,令她闖出了名堂,但單賣作品不夠生活,「我從來沒有做過全職藝術家啊!如果做全職,作品可能好不一樣。」她一直在教學,如今經營一家陶瓷教室,但疫情下一直在虧錢。近日忙於做村校項目,Sara 少了碰陶瓷,新作是藍曬及錄像等作品,到底是想讓自己放一個假,還是日後想作多方面嘗試?「我有個使命感繼續做陶瓷,陶瓷有給我一些東西,我像在跟它對話,我把它們變成一件衫,一塊樹葉,那之後可以做什麼?」
 My Mother(2009)
My Mother(2009)
 Time Traveler(2014)
Time Traveler(2014)
 Ceramic Dress(2011)
Ceramic Dress(2011)
 Leaving Falling as Songs Coming to my Mind, 2019
Leaving Falling as Songs Coming to my Mind,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