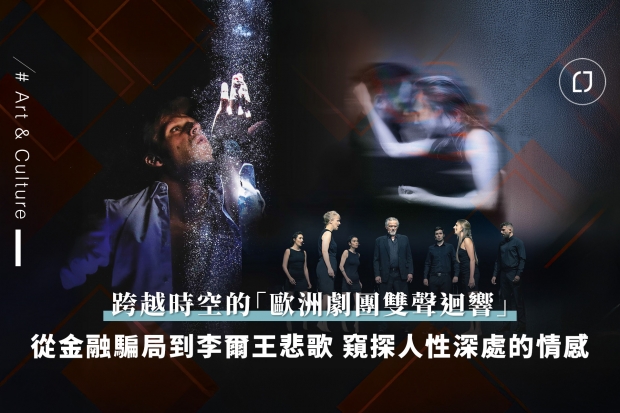陳果兩個腦 有戲就拍

在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入行,參與過無數類型電影。1997年陳果憑五十萬港元,一堆過期舊菲林拍出《香港製造》,震驚影壇。他拍九七三步曲,再拍妓女三步曲,在回歸祖國前幾年,這個胖嘟嘟的小子在商業類型片外,闖出另一種香港電影。數十年過去,他說那年頭跑影展大家都當他新星般看待。遊走於獨立與主流,拍片有好有壞,一直掙扎,2024年,成為今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焦點影人的他,笑說香港人都有兩個腦,一個搵食,一個作者腦:「總之有戲就拍!」
TEXT & PHOTO BY 何兆彬
場地提供:HKIFF
本來驚做唔到
問陳果作為今屆電影節焦點影人感受,他笑笑:「我本來驚做唔到,哈哈,結果又做到。我的電影社會性強,我擔心這個。我是香港導演群其中一份子,數下去始終都數到你,我覺得欣慰。」怕做不到是因為作品敏感?「對!會怕,因為時間不同,年代不同了。」
是次電影節選映陳果自1997以來十部電影,九七三步曲、妓女三步曲少不得,還有《餃子》(2004)、《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2014)等兩部較有商業片格局。這些作品是怎麼挑選出來的?「大家一起談。基本上,這次沒有放映我的主流作品,你知道,我們香港人兩個腦,一個搵食腦和作者腦,電影節可能較重視嚴肅的一面,就找了我嚴肅的作品吧。」他說這十部都有代具性,「《香港製造》不用多說,唯一一部比較商業的是《餃子》,它是最商業的一部,但是拍法上不是那麼商業。我讀過大陸的評論,說我用了藝術手法來拍商業片,我覺得當時我們拍沒有分的喔。明知是主流電影,但它的題材很多時候你不需要跟隨主流的類型的拍法。有些人覺得商業片就應該這樣拍,那樣拍,其實沒有什麼大分野。」
還有一部較有商業元素的是《那夜凌晨》,「《那夜凌晨》原著建立在一個流行框架上,影片的結構和故事敍事,其實就是一齣商業電影,不過由我來拍,扭了一扭,加入了社會性。比較下,《餃子》就真的沒有太大的社會性,純粹是女人為了要靚,不擇手段。」他笑了笑:「大家都知道2014年發生了什麼事。我們13年開拍,電影14年上畫,我覺得是不是真的很巧合呢!」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Golden Scene Company Limited /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Golden Scene Company Limited /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雋永不雋永
談到這一點,必須說陳果的電影中有種預言性,他更樂了,「當然有(預言性)。我們思考這個世界,你要想遠一點,想像十年後發生什麼事。1997年前香港人還沒醒,大家都在瞓覺,不太理(世事)。他們覺得你拍97?有無搞錯?有什麼好看的?沒有人會碰這題材。」談起《香港製造》,他多少有點驕傲。2017年電影滿二十周年,曾推出4K修復版,當時他說電影經過二十年,正好驗證是否經得起時間考驗,今天他說:「得嘅!我們拍這些電影,常會想到雋永不雋永的問題。其實我們做影迷的時候,會覺得很多導演很厲害,但今時今日重看,就覺得有些片經過時間洗禮,留不下來,那為什麼小時候你這麼喜歡?不明白的。」他的結論,是小時候年少無知,入世未深,以為好看就是好看,不會分析。
 《香港製造》Nicetop Independent Limited © 1997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香港製造》Nicetop Independent Limited © 1997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那你拍片時已有(雋永)這個想法?「不,我有戲就拍。拍完《香港製造》,它對我的影響很大,某程度上替我定了位置,這一點我那時候還不知道的,然後拍《那年煙花特別多》的時候,其實是用商業手法處理,再加入社會性。但拍完之後我覺得不是很好玩,其實它有商業化,但它不是成功的商業片,最大的問題是戲裡面沒有明星!老實說,商業片沒有明星,很難叫商業片!」他透露,當年華哥(劉德華)本答應找演員來參演,但最後「不敢」了,「他說你找新人拍吧,我就便宜一點去完成它。」《那年煙花》之後,他拍《細路祥》,就回到完全自己創作的狀態,不再融合商業手法,「我又把它拋下了,不要這些包袱了。純粹我想怎麼拍就怎麼拍。」及後這二十年,其實他一直遊走在商業在獨立之間,一如他自己說,搵食腦作者腦,兩者間隔運行。路要怎麼走,怎才走得遠,才拍到自己想要的作品,一直困擾着他。
香港米已成飯
陳果說,他當時創作思考的,是怎樣去講一個悲劇。
「能不能雋永這個點,那時候沒有怎麼想,也沒有那麼大壓力。總之有戲就拍,沒有計算,只是有一種心態,每一部戲的背景,都是一個悲劇的存在。」陳果:「我的電影悲劇性很強,但是我用一種看破人生、比較幽默的態度去處理,因為我很怕看悲慘的戲。所以,你看我的電影其實不是很慘,但它的深層其實是悲慘的。」他舉例說:以南下賣春妓女為主角的《榴槤飄飄》慘不慘?「大佬,那些女生說去搵食,即使你去問佢,佢都不會覺得慘,搵食啫!我定了人生目標,要賺這筆錢,問她慘不慘是大學生做研究才會問的,我不會問。這個很難,變成你拍的基調基本上都是來自低下階層,拍他們的掙扎面貌,但用一種不是那麼悲觀的方法去處理。」
九十年代尾那段日子,你每開拍一部電影,都源於一種創作的衝動,一個念頭?
「那時候很快的。當年市道還很好,你想到什麼就拍什麼。我得獎之後,獲得很多支援,那年頭的Art House電影/獨立電影的世界性還是很好的!有很多機會。」他苦笑:「但現在米已成飯,你再去要錢就很難了,這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他說當中除了電影市場改變,還有香港在地緣政治上受到的關注已不一樣,「香港還值不值得你這樣去做?這和時代有關,97前後,討論還是很闊,你還可以做這些事情,外國的資金也不少。但是過了幾年,香港每樣事情都米已成飯,人家就不關注你了,譬如人家面前有一部大陸片,一部香港片,他一定選擇大陸片!原因是你(香港人)不值得有什麼可以說了,我關心你都沒有用。雖然導演創作的主題、方向都重要,但有時電影節會針對地域性的政治氣候,以前香港還有一點被挑選的機會,現在好難!」
 《榴鏈飄飄》© 2000 Studio Canal France And Nicetop Independent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榴鏈飄飄》© 2000 Studio Canal France And Nicetop Independent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導演先別想得獎
九七後那幾年,他創作力旺盛,不斷拍片,不斷跑世界影展,被視為藝術新星,「我自己也想不到,剛拍完電影,第一次出門,發現人家看你已不一樣。他們覺得,你這個戲怎麼這麼有力量,我自己很難解釋。」阿果笑說,自己不敢開臉書,因為網民/影迷太熱情,「你沒有想過自己有這種影響力,以前我們拍完戲就算,但去完韓國、日本、大陸等地,才發現(作品)原來真的有迴響,神推鬼㧬,決定了你要走這條路。其實如果我沒拍三步曲,也許很快轉了軚,拍什麼《拆雷》、《拆彈》也可以!」
電影工業出身,其實要拍你一定懂得拍吧?「我們主流出身自然會拍。」沒走這條路,是什麼原因?是自己推了,還是機會沒有來?「一半一半。那時候我立刻開拍《去年煙花特別多》,主流電影公司很少會讓你拍這題材,講回歸,又打劫,有什麼好看的!」
一直在商業和獨立之中浮游,陳果的商業片一直不太成功,為什麼?「不成功有很多原因,譬如老闆多方面改動電影,這是很難的。如果你給我自由發揮拍一部商業片,我不會覺得不成功,因為我們自由慣了,不被人管。」但由你來拍商業電影,還是要加入大量陳果風格吧?「一定是。但最衰的是,我們在工業中成長,永遠照顧老闆,尤其是做副導演出身的這些人,不是一出來就做導演總是一副『關我什麼事』的姿態。我們瞻前顧後,顧老闆感受,有時候反而沒有我拍自己作品那種執着,這才最難。」
舉個例,以沒有選映的《九龍不敗》為例,大家期待它就是一齣純粹官能性的商業電影,由頭打到尾,但結果它像一齣Cult片,「不,《九龍不敗》本來有很多文戲,但都被剪掉了。這齣戲有人讚有人踩,其實老闆剪了我很多文戲,我是很忟的,講起都忟,但問題是我又很明白老闆的選擇。其實你早點跟我說嘛!我多拍點打鬥不就行了?」但戲中張晉騎着龍衝到岸上,那根本不是主流商業片的拍法吧?「所以我就想超越他們的想法!其實那個是十年前寫的劇本,當時甄子丹很喜歡劇本,答應了主演,但一個商業片,由A談到B再談到C的時候,這個人不喜歡這個部分,那個又不喜歡那個部分,劇本一直修改,到完成時,你有兩條路走,一是對,一是錯!你明白嗎?」那它是對或錯?「我不知錯不錯,有些人讚我,就叫做錯唔晒。那個戲很難拍,特技不夠錢做就死了,如果回去用我自己的版本,一定不會比現在差。問題是我沒有辦法改變老闆的思維,就只能這樣。」
票房或意圖上,《九龍不敗》是失敗了。數年前問陳果電影路要怎麼走,以獨立電影成名的他,堅持說還是要拍商業片,如今年過六十的他,今天說若有機會,一定還會拍商業片。
「新導演會跟我說:我想拿獎!我會跟他們說,你先別想這些,你先拍好一部戲。路很難走,你不如拍一部商業片,站穩腳,儲點資源,慢慢再做,否則你永遠無得做!」你自己拍獨立片成功,由你來說沒有說服力吧?「我說才有說服力,我拍獨立成功,但獨立電影搵唔到食!成功是空的。香港拍獨立片,搵到食,只有我。拍藝術片不成功,等於零。藝術片、商業片一樣,你成功才證明到你行,若你以為藝術片不成功會有光環,那我要告訴你:不,兩者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