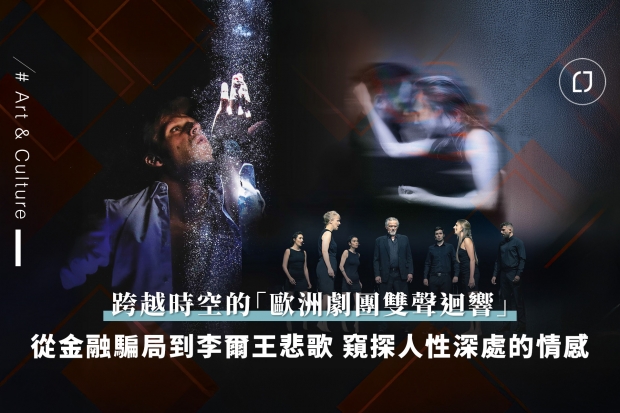Club C+ Modern Oriental的私家空間

在餐飲業及服務業擁有豐富經驗的梁力恒(Nicholas)可說是私人會所的專家,除了於2021年的疫情期間開設以雪茄、中菜、美酒及藝術為主題的Club C+之外,亦為2023年開設的新生代會所Whale Club的顧問及成立團隊之一;加上本身從小到大都出入香港一些較傳統的奢華私人會所,以及向來受設計品味的薰陶,相信Nicholas對私人會所有獨特體會。
TEXT BY JAZ KONG
PORTRAITS BY BEN TAM, CLUB IMAGES COURTESY OF CLUB C+ AND WHALE CLUB
 Club C+ 創辦人 Nicholas,同時亦為 Whale Club 顧問。
Club C+ 創辦人 Nicholas,同時亦為 Whale Club 顧問。
Club C+: Home Away From Home
訪問當日,Nicholas身後的正好掛着來自季豐軒的Lalan謝景蘭作品,順勢就談起藝術來了,發覺季豐軒的季小姐原來就是C+的藝術品策展人,不時會為會所轉換來自中西方藝術家的作品;除了重視藝術之外,C+亦有指定的頂尖花藝設計師Gary Kwok、燈光設計師Tino Kwan,當然少不了Nicholas的設計大師父親Steve Leung的室內設計,以及由Alan Chan負責的branding。Club C+這個名字有多重意思,第一就是中文讀音跟「雪茄」類近,顧名思義,這就是一個可以品雪茄的會所;第二就是「私家」,簡單來說,就是一個home away from home。位於中環都爹利街樂成行,窗外可以看到雪廠街,附近亦是律師樓、醫務所等專業人士的中心點,Club C+雖然面積不大,會員數目也限於大約60人,入會費二十萬港元(雖然Nicholas亦提到未來可能會增加年度會員制),這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家」?
幾年前第一次接觸到Club C+,無可否認是有點錯愕的,驚訝的位置在於雪茄club配中菜這回事。C+的菜式全是大廚Angus陳定邦師傅的拿手好菜,經驗豐富的他來自利苑、Mott32等著名餐廳,除了名貴菜式之外,Angus跟Nicholas更希望為會員提供家常便飯如燉湯、蒸魚、咕嚕肉等。「選擇提供中菜,最老實的原因就是因為自己喜歡吃中餐,尤其是年紀增長,就愈來愈依賴,跟太太去歐洲旅行時,第三日就開始找當地的中餐吃飯;畢竟中餐比較有家庭的感覺,這就是我們做中餐的原因。第二,根據我的個人經驗,現時普遍的雪茄吧都是比較英式的設計;但我希望我的會員可以在這邊留長一點的時間,而非抽完一枝雪茄就離開。做西餐的話,意粉也好扒類也好,一星期最多只會吃一兩次吧,若然要他們有傾向每日都在此吃飯,就要做中餐。鮑參翅肚都會做,但很多時候見到的現象,是客人會選比較家常的菜單,燉湯、蒸魚、蒸肉餅都是我們的標誌性菜式,好像真的回家一樣。第三就是,雖然我們不想走英式風格,但中式也不代表一定要很oriental。在視覺設計上都呈現出當代演繹的中式設計,用上橙色感覺很舒服;例如門上的方圓設計就是重現了以前宮廷裏面的Moon Gate;玻璃窗上貼的橙色是想製造黃昏golden hour的感覺,時間在夢中在不知不覺間流逝。」
 Club C+ 雖然面積不大,但每個房間都可以隨時因應會員的需求而作出變動,團隊在設計上亦花了極大的心思,去為每間房做好通風系統,應付不同的場合及需要。(圖片由 Club C+ 提供)
Club C+ 雖然面積不大,但每個房間都可以隨時因應會員的需求而作出變動,團隊在設計上亦花了極大的心思,去為每間房做好通風系統,應付不同的場合及需要。(圖片由 Club C+ 提供)

對Club C+而言,「social club」好像不太應用得到,還是「private membership club」比較適合,即使兩個字有類似的意思。Nicholas直言,C+針對的會員都是以Old Money為主,「C+的模式偏向傳統會所模式,都是指向比較well-established的會員,跟Whale Club吸引的一班較年輕、較喜歡擴闊人際網路的new money群體形成對比。當然地,我們的門檻亦會相對提高,二十萬港元的入會費,變相獨特性及私隱程度都會相應地高一點,也會提供相對優質餐飲等服務的要求。我們沒有多餘的娛樂設施,不能唱卡拉OK、也沒有Poker枱等,純粹是一個很私密、環境很好、質素很高的會所的傳統模式。」話雖如此,Club C+卻有別於成立多年的殖民時期較為嚴肅的會所,「我年輕一點的時候,都有幸地接觸到不同的會所,以Hong Kong Club為例,他們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傳統的會所,在穿著要求上如是,或者不能在場所內講電話、用手提電腦工作等;當然,這是時代的產物,這個privilege是有價值的,保留傳統也是理解的;但既然時代改變了,自己也不是喜歡每日都正裝打扮,所以一開始成立Club C+時,都決定不要走太傳統的路線。」正如C+現時的會員分布都在打破大家、打破Nicholas對雪茄的刻板印象,「我的確是有點驚喜的,就是我們的女士會員都佔了整體約兩成。以往雪茄可能是爸爸、爺爺那一輩才會抽,但的確是見到年輕化的趨勢,我認識身邊很多女士都會對這件事有興趣,即使未必是每天吃,他們都開始接受的程度會大一點。」
面對現時慘淡的餐飲業,加上近年私人會所的湧現,Nicholas卻好像不太擔心,「疫情期間的確是有史以來最高收入的時期,困住在家,大家都想逃離一下,但同時又要求高的私隱程度;這也是我們成立的動力。」Nicholas認為,C+也好,會所也好,好處是大家會被記住,例如員工會好好記得會員喜歡吃什麼、不能吃什麼,這些服務並非一般餐廳可以提供到的。「不論餐廳也好、會所也好,競爭一直都在,但只要找到自己的獨特性(niche)就可以了。以前說自己是某個會所的會員,好像是一個身份的象徵;但現代人追求的偏向像體驗,私人會所就可以提供到這種個人化的服務。」
 大廚 Angus 陳定邦師傅為會員造出一道道拿手小菜,由山珍海味到家常便飯,都一一照顧得到。
大廚 Angus 陳定邦師傅為會員造出一道道拿手小菜,由山珍海味到家常便飯,都一一照顧得到。


Whale Club : What's Next?
有趣的是,Nicholas同時在協助中環另一家新晉會所Whale Club(WC)的營運。Whale Club這個名字本身就跟虛擬貨幣有關,在crypto的世界,鯨魚就代表領袖、或者期望自己能成為下一個leader的人。同樣位處中環,但坐落擺花街的Whale Club就是一個截然不同的風格及空間,「WC的主軸是pioneering ideas,會員可能是年輕一點的,喜歡交際、喜歡networking的人,是比較希望尋找更多更新的機會,所以酒吧、gallery的位置都會促進對話的產生,會員甚至可以在app上跟其他會員買賣手上的雪茄。但我們說的前衛,就好像是20年前講信用卡一樣,當時是一件天方夜譚的事,但現在就成為了我們的日常;我們的創辦人團隊都認為虛擬貨幣是差不多的概念,現在好像是個新現象,但五年、十年後就可能成為我們的恆常。我們不是鼓勵會員炒作,只不過我們要準備未來,到cryptocurrency真的恆常化、比八達通更通用,人人都有crypto wallet時,我們就早已準備好可以隨時配合,這些就是其中的pioneering ideas。」
Community不同,在空間的設計和提供的設施都大有分別,「WC的思路是完全不同,他們所講的,是未來的趨勢是什麼、接下來有什麼新意念新科技新模式,也可以說是一個clubhouse。所謂的new money會員,不只是年紀上,而且是喜歡擴充網絡的,需要見更多的人、put themselves available的,配合這個需要,酒吧位置及座位非常闊落,房間也有卡拉OK、有Poker枱,相對上也有更大的酒窖及更豐富的藏酒。」相對C+的九成會員都同時擁有幾間會所會籍,WC吸引的,可能較多是首次接觸會所的社群。
對於後疫症時期湧現的會所,Nicholas形容這個趨勢是回應了大家「徘徊在很I(introverted)又很E(extroverted)的狀態,脫離疫症期間的隔離,大家很想重投自己的community,想開始接觸這個世界、卻又同時很喜歡那種隔離的感覺。COVID是很極端的,硬生生地將一班很E的人困在家,被逼不能動;但其實什麼人都好,都已經習慣及找到了靜靜地留在家中那種感覺,是一個很好的reshuffle機會;同時也造就了會所的興起,不同的會所正好是外向和內向的平衡。」到頭來,Nicholas形容私人會所為human business,重點都是維持community,到頭來,人還是會找一個容得下自己的地方。
 Whale Club 的設計、設施及會員活動都旨在促進會員之間的交流。(圖片由 Whale Club 提供)
Whale Club 的設計、設施及會員活動都旨在促進會員之間的交流。(圖片由 Whale Club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