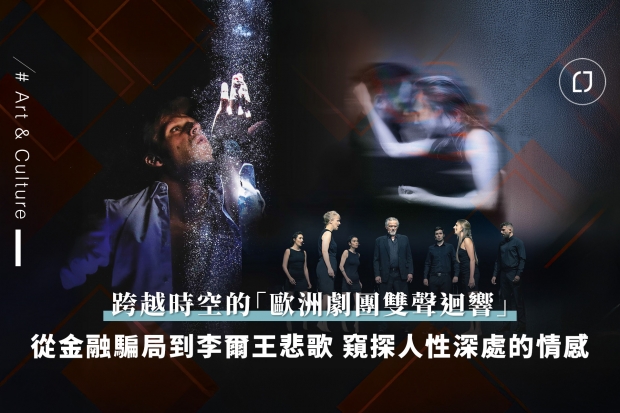橫跨三十萬年的人類與人類+

TEXT BY JAZ KONG
IMAGES COURTESY OF VILLEPIN  策展人Arthur de Villepin及藝術家井田幸昌(Yukimasa Ida),在讓人迷失的太空中,方舟成為了盛載着人類的太空船;來自四方八面的光與鏡代表了迷失後的新世界,審視人類和時間及自然的關係。
策展人Arthur de Villepin及藝術家井田幸昌(Yukimasa Ida),在讓人迷失的太空中,方舟成為了盛載着人類的太空船;來自四方八面的光與鏡代表了迷失後的新世界,審視人類和時間及自然的關係。
迷宮中,人vs獸vs科技
《DAY ZER0》展覽的第一站開始於遙遠的未來,在科技在AI的發展下,人類的身份和生活不斷改變,甚至被扭曲或重塑。甫踏進Villepin畫廊,就見到Arthur de Villepin設計成漆黑一片的太空,唯一的燈光只落在雕刻和畫布作品上,地面及天光刻意沒有一絲光芒,若然踏入畫廊前是陽光普照的下午,雙眼還真的需要一段時間的適應;策展人蓄意讓大家迷失在未知當中,步步為營。對藝術家和策展人而言,讓參觀者迷失的意義在於尋找,Arthur在展覽中就提到「在尋找的過程中,往往先會覺得失去了什麼的,從而有慾望去找到更多;這就是改變的過程,而這一層的主題就是轉化。」
 藝術家井田幸昌(Yukimasa Ida)
藝術家井田幸昌(Yukimasa Ida)
既然要探討人類的身份認同,就一定要有井田幸昌的經典人像作品。井田幸昌寫道,「我認為人類的存在是可愛、愚昧、脆弱、卻又美麗的。」在這裏就躲藏着井田幸昌為展覽創作的最後一件作品,以希臘神話中的Minotaur為主角:那為什麼這個牛頭人身的故事人物會在30,067年出現?由牛頭怪而帶出的「自我認識及發掘的過程」,猶如在迷宮人的牛頭怪,在這個未知的世界裡,在面對困難的時候,大家會選擇走向人性的一面、還是獸性的一面?對的,人類是可以選擇的,尤其在科技洶湧來襲的年代,有時我們會反抗、有時會接受、甚至擁抱某些新概念。一切都是構成新身份的機會。就像以David Bowie為靈感的另一幅作品,是男是女是什麼身份都不太重要,蛻變就是這麼一回事;加上科技日新月異,唯一能肯定的,是未來的不確定性。在三萬年後的世界裏,「人類」會以什麼形式出現?現在的社交媒體、科技、AI等會否取代人類而讓我們變得less human嗎?井田幸昌就反問道,「所謂『人類』的定義是什麼?在進化的過程中,所謂的改變其實只有很少,一百、一千、一萬年前的人類是人類嗎?我覺得AI只是人類在歷史上有化改變的一部分而已,差不多像原始人至今的一個生物角度上的轉變。」 井田幸昌以David Bowie這位音樂傳奇人物帶出了人類的不同面貌——面對不同,人類要怎樣擁抱這份不同?若然individuality是人類的特性之一,在科技在AI下,人類又怎樣才能保持這份獨特性?
井田幸昌以David Bowie這位音樂傳奇人物帶出了人類的不同面貌——面對不同,人類要怎樣擁抱這份不同?若然individuality是人類的特性之一,在科技在AI下,人類又怎樣才能保持這份獨特性?
重新出發的決心
離開地面展覽層,Arthur de Villepin帶大家逃離黑暗的太空,延續井田的探索之旅。對井田而言,繪畫和創作其實是他思考過程的一部分,「人類的生、死、生命的循環都是一些讓我一直在思考的題目,然而,我還未找到答案、也不認為會有答案,可以做的,就只是不停以此作為任務,將尋找答案變成自己的旅程,也將不同的問題和思考紀錄在作品中。」
這一層的「方舟」以四面八方的鏡面裝飾造就出一個不斷延伸的世界,代表大自然中的生命循環。策展人表示,若然地面一層講人性講身份,將其碎片化,就變成了cycle of life,亦即大自然;而鏡子則希望為大家帶來不同角度去觀察生命,明明在前面的畫作,很有可能其實是在你的背面或上面出現——這個不只是大自然,而是一個正值改變的大自然。而我們所身處的世界也剛好如此,變化是永恆而巨大的,人類若然執着於見山是山、見樹為樹、要「認知」眼前的一切風景,在劇變中的世界是幾乎沒有可能的。井田再進一步解釋,「去理解、去質疑自然,其實是沒有可能的;因為大自然就是一切——我們所吃的、我們所感受到的、甚至是我的顏料,一切都是來自這個世界,這就是人類的靈魂跟自然連結的印證。」
這一層的作品多為風景畫,技巧上跟井田的人像畫其實如出一轍,將顏料一層一層疊起,形成抽象、豐富而有層次的風景,將井田在西班牙、在印度等不同地方旅行的景色,以他的認知呈現。在此之中尤見重要的是一幅像窗口的作品,井田除了運用了不同的畫筆、筆觸及質感之外,其實「大自然」亦隱藏了在畫作當中:細看之下,會見到井田以樹葉為筆而畫成的筆觸。井田記得當時在倫敦畫下這幅作品時,心想它一定不會比真實的大自然景觀優勝(win),所以見到身旁的大樹,就決定以樹的一部分為畫筆,讓大自然的足跡更顯而易見。這其實也印證了井田深信的「一期一會」(Ichi-go ichi-e)的哲學,「這是我22歲去印度旅行時所得的感悟,覺得世界上的每件事物都總是在變,地球亦如是;但在某一些特定的因素下,成就了不同的當下。所以,作為藝術家,我希望可以將這個時間點記下,因為每一刻都來得獨一無二;將這個概念套在作品上,即使用畫筆也好、樹葉也好,這個時刻都是自由的,所以我希望以此為例子,根據每個當下,在畫布上自由自在地創作。」但井田認為這個概念或做法只是很純粹的一個方法,沒有好與壞、對與錯,「一期一會並不是鼓勵大家享受當下,不是要享受,概念講的只是『當下』的重要性,不需要為這一刻感到快樂與否。」正如大自然中的生命循環一樣,井田認為「不是生存或生命就值得高興;相反,死亡也不是悲傷的事。對大自然來說,這些只是自然不過的事情。」 來到展覽最高的一層,Day Zer0以Stanley Kubrick的《2001太空漫遊》為靈感,以環境及畫作帶來出破壞、未來與改變等主題,而作品則同時展示了過去、現在及未來。在象徵達爾文的進化論的作品旁邊卻出現了「神」的形態,同時帶出了對一個被AI充斥的人類未來的疑惑。
來到展覽最高的一層,Day Zer0以Stanley Kubrick的《2001太空漫遊》為靈感,以環境及畫作帶來出破壞、未來與改變等主題,而作品則同時展示了過去、現在及未來。在象徵達爾文的進化論的作品旁邊卻出現了「神」的形態,同時帶出了對一個被AI充斥的人類未來的疑惑。
重生
再往上走一層,來到展覽的最後一部 分:「零日」。跟地面黑暗的展廳作出強烈的對比,「零日」以Stanley Kubrick的《2001太空漫遊》為靈感,有點熱力有點刺眼的(像冰冷實驗室)的白光從腳下擴展到整個展廳,瞬間將大家帶到聖地(thedivine)。井田毫不猶豫地表示,他是相信有「神」的存在,但這個信念是沒有特定的宗教指向的,也不會依賴神,就只是單單相信有造物者的存在而已;像日常生活中,井田會經常到神社參拜,也會祈願,但就不會將生命或創作依靠神。因此,當來到這個神聖的領域去繼續深入探討人類的未來時,他並不是希望要決定、也沒有這個能力去決定到底什麼人類的特質值得被傳承,只是希望透過不同的作品,帶出即將會有篩選、淘汰及改變這個事實。
策展人Arthur就以Prometheus去比喻井田,「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偷了天火送給人類,象徵給人類帶來真相;而這也是藝術家的職責。在展覽中,井田以作品為他的證詞,講面臨改變的未來要如何保持希望。」Arthur覺得現今文化對所謂的神聖有點迷失:在改變來臨之前,人類可能會感到害怕;在經歷改變的途中,我們可能會不知情;但當未來慢慢浮現,人類就終於會開始相信。這一層見到的一幅作品正好在講述過去、現在及未來同時發生及互相牽絆的關係。在這幅以Gustave Courbet的名作《L'Atelier du peintre》為靈感的作品中,井田將未知的未來化成一個戴着面具的角色,這是他還是它(機械人),井田讓觀眾自行定義。「作品入面用了很多不同的符號去表達我想講的訊息,其一是入面的小孩子代表了未來。在創作中過程中,我投放了很多情感在這幅作品,因為當時我的祖母去世了,看着上一代的年老及離去、以及下一代的出現及成長,不禁會聯想起生命的循環及延續。小朋友有無窮無盡的可能性等待着他們,而他們將來要面對的世界也跟我們所面對的截然不同,這個life cycle是很特別的。」井田見證長輩的離世,想像家中的小朋友將來也會像現在的他一樣,見證自己變老;這個過程是很圓滿的,而他認為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若然要看到未來,就必須同時看清過去;想對未來有希望,就必須也要了解過去及現在的絕望,它們是同時存在的。」
回應踏進畫廊時所見到的幾個代表人類文化及文明的雕像,以及人類的未來,井田想問大家,「你認為神是什麼?」神、人類、現實、虛擬世界,一切有定義嗎?「我們現在每日對住手機及不同的科技和機械,這不也是虛擬世界嗎?我們見到的,也並不完全是『現實』,只是一個2D的代表,也不是『自然』的;但我們卻透過這個平台,去接觸其他人、這個世界及不同的資訊,再從中思考。在這個世界裏,我們不需要有表情才算是一個真正的人,只是一個符號。所以,我在畫中只以一個光影去代表神聖,也可以理解為AI世代跟人類的距離。」
另一個有趣的事情,是在同一層的作品中,就出現了兩個現階段仍普遍被仍為是對立的概念——宗教和進化論:有神的象徵,有亞當和夏娃的代表,也有代表達爾文進化論的猴子。策展人特意將它們放在一起,科學和宗教,對我們有什麼關係及影響?正如亞當和夏娃的蘋果,它代表了改變,也可以是「apple of love」,正如我們的現世界,充滿不同的可能性及解讀。
井田化理解及表達的人類是一個複雜的生物,所謂的「人性」也不能簡單去理解。問到井田認為人類最基本的身份是什麼,他毫不猶豫地說,「是desire,像 《Minotaur》中的主角一樣,半人半獸,可能這就是『人類』的本質。」正好《Minotaur》是井田為是次展覽畫的最後一幅作品,以疑問作結:人類到底會傾向哪一個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