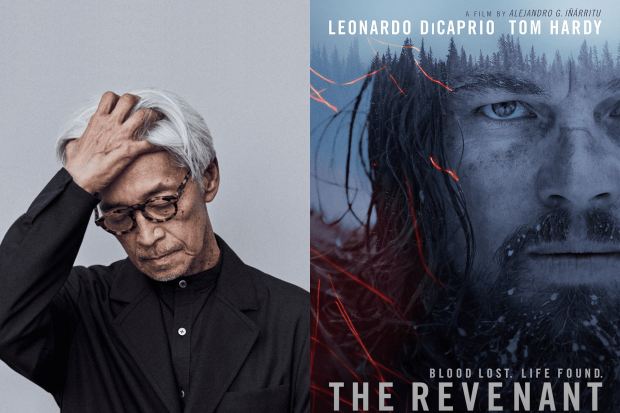Larger than Life 的八十年代香港
 Greg Girard, Chow Yun Fat on The Eighth Happines s(《八星報喜》), Tsimshatsui, Hong Kong 1987
Greg Girard, Chow Yun Fat on The Eighth Happines s(《八星報喜》), Tsimshatsui, Hong Kong 1987
TEXT BY 何兆彬 PHOTO COURTESY OF BLUE LOTUS GALLERY
 Greg Girard, Woman at tram stop, Central, Hong Kong 1985
Greg Girard, Woman at tram stop, Central, Hong Kong 1985
「就如任何『黃金時代』一樣,往往直到很久以後,你才會意識到自己曾活在其中。或許八十年代如此特別的其中原因是流行文化,尤其是那個時期的電影和音樂,為定義當時的『香港』發揮了巨大作用。」Greg Girard說。
曾在港居住多年,訪問時身處在溫哥華附近的Girard,過去20個月一直在努力創作,及製作好幾本新書。同時,他的攝影展《HK UNSEEN》在香港開幕,怎麼會有這次個展?「我在七十年代來港時,及1982-1988年居港期間拍下好多照片,當中一些作品後來出現在以九龍城寨為主題的《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City of Darkness Revisited)以及另一本攝影集《HK:PM. Hong Kong Night Life 1974-1989》(香港夜生活視角)當中,但還有大部份作品從未曝光。」這些作品,記錄了他的年輕歲月,他的難忘回憶,也是他眼中香港的黃金年代,「城市總有它的美好時刻(Moment)。命運、歷史、運氣,不論任何原因,鮮有按計劃地令一個城市會變得Larger than Life,八十年代的香港正是如此。」
 Greg Girard, Club Gold Star, Wanchai, Hong Kong 1993
Greg Girard, Club Gold Star, Wanchai, Hong Kong 1993
 Greg Girard, Natham Road Crossing, Hong Kong 1987
Greg Girard, Natham Road Crossing, Hong Kong 1987
加拿大溫哥華生活平靜,但也許有點太過平靜,在這裡出生的Girard坦言,成長時身處加拿大郊區,一直等不及要離開。
18歲那一年,他跳上了貨船,船經由三藩市出發,穿過太平洋,來到香港,「船程十八天,貨櫃船由三藩市越過太平洋,當我們穿過鯉魚門進入維港,映入我眼簾中的是筲箕灣、北角那些飽受風雨的高樓大廈。」Girard這段初戀,經歷數十年仍然記憶猶新:「我記得入境處的職員登上貨船,給我們扱印做手續,我坐上了街渡,在尖沙嘴公眾碼頭上岸,走上彌敦道,找了一個地方入住。我住的可不是重慶大廈,而是再上一點,美麗華酒店附近的招待所,一切就此展開。」他記得在香港的第一個晚上,聽從在船上菲律賓水手推介,到了漢口道一家名叫黃色潛艇(Yellow Submarine)的酒吧消遣。因為成長時一直住在溫哥華郊區,他從來沒去過酒吧,不知道該點些什麼來喝,「於是我叫酒保給我介紹,那個晚上,年輕的Greg喝了點Campari和汽水,醉醺醺地離去。」
 Greg Girard, Sheung Wan, Hong Kong 1975 (Detail)
Greg Girard, Sheung Wan, Hong Kong 1975 (Detail)
做拍攝工作,當時來說,這是有點夢想成真的,我終於能以攝影賺取生活了!」
過了一兩年,他轉為自由身攝影師,替《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等國際雜誌做拍攝工作。「通常我有一半時間我身在外地,在鄰近地區做採訪,有一半(或更少)時間我會留在香港,接不同的工作。」
值得保留部分城寨
新聞攝影不能滿足年輕的他,他同時開展自己的拍攝計劃,例如到城寨拍攝。後來與建築攝影師Ian Lambot (林保賢)合作,出版記錄城寨的名作《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一書。回顧年輕歲月,他說:「像很多找到路來港的人一樣,你也可以說是香港成就了我。」
Girard鏡頭下的城寨,意外地受到注意。九龍城寨早在1847年清代建成,本是駐軍基地,1899年後漸漸成為無政府狀態下的圍城。城寨多年來被稱為三不管地帶──港府不敢管、英國政府不想管,中國政府不能管,裡面充斥着黃賭毒,妓院、煙館林立,無牌牙醫盛行,也是幫派的大本營。1987年,港府公布清拆計劃,這一年,據統計城內居民達五萬人。城寨在1993年完全清拆,Girard是少數詳細記錄這傳奇之地的攝影師。
城寨消失,但傳奇縈繞不散,一直在網絡及被民間討論。今天回望,Girard仍然興奮:「(城寨)相當迷人!香港的細路總聽到父母告訴他們別去,別聽他們。」他說當年人們都問自己是否該保留城寨,他曾答「否」,但今天答案會有所不同,「當時我答『不』是因為健康及安全原因,即使它那麼迷人,它不是一個你會要求別人居住的地方。」
他續說:「雖然這麼答過,今天回望,我現在會認為部分城寨是值得保留的,以此作為紀念及榮耀香港最有復原能力社區的歷史試金石。若有遺跡留下,這麼致敬,會令今天的港人能夠更了解當年人們住在城內是怎樣的。」這麼一說,顯露了他一直的創作動機,Greg Girard的作品一直被視為記錄和反映城市的社交及地貌變化,顯示了城市的現代性。
 Greg Girard, Arriving Kai Tak Airport from Beijing in June, Hong Kong 1989
Greg Girard, Arriving Kai Tak Airport from Beijing in June, Hong Kong 1989
2011年他回到溫哥華,驚訝於這個出生之地的變化,後來他把早期(1972-1982)早期拍下的溫哥華照片出版成書,當中一些最早期的作品,是早在他高中時拍攝的。1986-1992他拍香港九龍城寨,2000-2006年他拍上海,2009-2010年拍越南河內,及後拍攝日本沖繩。這些吸引他拍攝的城市都有一個特點:它們都是港口城市。
他一直拍攝人的居住環境,城市景觀的變化,他曾說過;「人在年輕時總以為世界是一個模樣,固定不變, 但最後總發現世界在不停變化, 一直變形(Transform)。」他承認談到上述這段話,想到的正是香港,但它也切合其他城市。
「你說得對,我往往受港口城市迷住了,我也搞不懂為什麼。不錯,我在溫哥華長大,它也是個港口城市,雖然我一直等不及要離去。也許港口城市就是人們聚集的地方,在此處陌生人也變得正常。」問他一直想用相機在這些
港口城市做點什麼,他答得極富詩意:「我利用相機嘗試做的,是我一直想把世界據為己有(make the world my
own)。」
曾居港數十年,視此地為家,他怎樣比較1974年初來香港、形容為黃金年代的八十年代,跟今天2021的香港?「回答此問題的一個方法,是去比較1974年和今天市面上書寫香港的書。在1974年大概只有兩本書接觸到西方讀
者,一本是《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 1957),另一個是《生死戀》(Love is a Many Splendored Thing,1952)。如今再寫一個書目,列表上的作品可是無窮無盡的。」
拍下那麼多只能回味,不能回到的過去,如能穿梭時空,他會回去八十年代的香港拍點什麼?他可曾遺憾沒有拍下
什麼?「但願我能拍下八十年代那些舞廳(ballrooms and dance halls)。我戳自己的腦袋,我一張也沒有拍下來。」Greg Girard還會回到香港嗎?他答得相當肯定,「當香港通關我就會回來,開展另一個計劃,大概會是2022年吧。」
《HK UNSEEN》
展覽日期: 即日起12月12日
展覽地點: Blue Lotus Gallery
上環磅街28號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