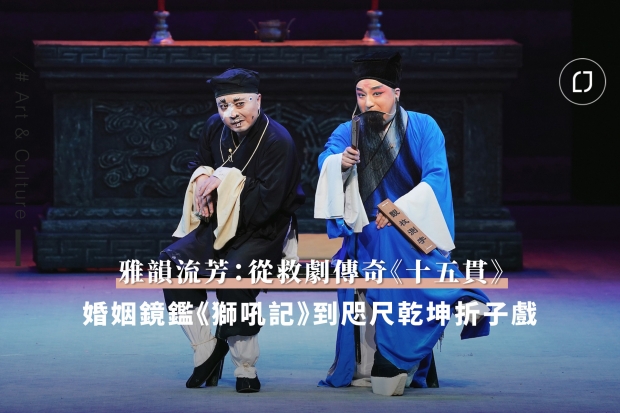港式奶茶何以得寵?
 製作奶茶有如儀式,包括「撞茶」、「拉茶」及「焗茶」,一杯上好的奶茶工序繁複,各有不外傳的秘方。
製作奶茶有如儀式,包括「撞茶」、「拉茶」及「焗茶」,一杯上好的奶茶工序繁複,各有不外傳的秘方。
坊間還有一些較為古老的茶餐廳(冰室)仍沿用「港式奶茶」的舊名稱──「西冷紅茶」,名為「紅茶」,實為「黑茶」(black tea),而「西冷」之名,源於錫蘭(Ceylon,今日的斯里蘭卡)的音譯。
話說原名李霖的香港新文學健將侶倫(1911至1988年)的第一本散文集就名為《紅茶》,出版於1936年,憶述在當時的文藝聚會中,「文青」一邊飲紅茶,一邊談文說藝;由此可見,「紅茶」在本港盛行了至少有七八十年。
 「港式奶茶」又名「絲襪奶茶」,那是指將煮好的「紅茶」用棉線網過濾,隔去「茶渣」,紅茶因而更覺香滑。
「港式奶茶」又名「絲襪奶茶」,那是指將煮好的「紅茶」用棉線網過濾,隔去「茶渣」,紅茶因而更覺香滑。
《紅茶》所收錄的散文,最早寫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記述了當年侶倫等一班「文青」之嘆「紅茶」,乃是一種充滿異國情調的生活情趣,他們在九龍城邊上的海濱漫步,然後走到小冰室裏飲紅茶。
1929年夏天,葉靈鳳與妻子郭林鳳經港回廣西,在侶倫的九龍城居所家住了整整一個月,他們都以食物來互相稱呼:葉靈鳳叫做「醬油」,郭林鳳叫做「辣椒」,侶倫就叫做「紅茶」──九龍城如今早已變貌了,侶倫、葉靈鳳亦早已辭世了,然而其時可謂人文薈萃,此一段「紅茶」佳話也隨而湮沒了,教人思之惘然。
「港式奶茶」又名「絲襪奶茶」,那是指將煮好的「紅茶」用棉線網過濾,隔去「茶渣」,紅茶因而更覺香滑,再加入淡奶和糖,據說始創人是蘭芳園的林木河。
他沖奶茶時使用特製的白布袋,其後沖奶茶所用的棉紗網屢經改良,鑲有金屬框架,而製作工藝有如儀式,包括「撞茶」、「拉茶」及「焗茶」(金屬茶壺加蓋,以小火來「焗」),一杯上好的奶茶工序繁複,各有不外傳的秘方──選用茶葉的比例、「沖茶」的手法乃至「焗茶」的時間各有不同,可以說是各師各法,故此沒有兩家茶餐廳的奶茶的滋味是完全相同的。
奶茶製作技藝是一門學問,有說茶是骨體,奶是肌膚,一杯上乘的奶茶要有「茶瘦奶肥」的上乘品質,濃稠得宜,奶和茶的香氣層層分明,還要加糖。
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大概就不能領略「港式奶茶」的好處,他在《一杯好茶》(A Nice Cup of Tea)中就有此說法:「你怎能稱自己為一個真正的茶的愛好者,如果你喜愛在茶中加糖的話?」他認為那就等於加胡椒或加鹽,因為茶合該是苦澀的,一如啤酒,「如果你將它甜化,你就不能再品嘗茶味了」。
 艾米爾.巴恩斯在《如果茶杯能說話》一書指出茶本身溫暖而舒適,總是煥發着放鬆的情緒,從而分享着信心。
艾米爾.巴恩斯在《如果茶杯能說話》一書指出茶本身溫暖而舒適,總是煥發着放鬆的情緒,從而分享着信心。
奧威爾這番話也許不無道理,但「港式奶茶」卻是另一回事──重點在於「奶」和「茶」的配合,加糖固佳,不加糖亦無傷大雅,因為品評奶茶有四大準則:「望」之,色澤要飽滿,「聞」之,氣味要有迷香,「呷」之,質味要濃郁,「吞」之「嗒」之,幼滑而舌尖留有餘韻,此所以能夠迷倒港人(乃至外來者),歷久而成非物質文化遺產。
「港式奶茶」自有它的道理,英國戲劇家亞瑟.威格.比羅奈(Arthur Wing Pinero,1855-1934)說得好:「有茶的地方就有希望」(where there's tea there's hope),這句話如果套用於香港,大概可改為「有奶茶的地方就有希望」。
著作等身的艾米爾.巴恩斯(Emilie Barnes)在《如果茶杯能說話》(If Teacups Could Talk)一書則指出:「備茶和侍茶的每一個動作都鼓勵對話」,因為嘆茶的時間儀式化了,充滿對話的可能,「即使是茶的本身,溫暖而舒適,總是煥發着放鬆的情緒,從而分享着信心。」這番話大概亦適用於「港式奶茶」。
撰文︰占飛